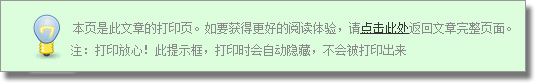诗意江南
三月里啊好听江南雨。淅淅沥沥的像一千多年前唐朝女子拨弄的丝弦。有淙淙的音还有颤颤的形。这时候我的江南就多了男人穿蓑衣,女人打花伞的景致。在薄雾轻烟里行走,不用捕捉,诗意就从心里冒出来,且一首《三月里的小雨》便在心里浅吟低唱了。而这雨也真能,下久了便叫梅雨。或许梅花便是叫它唱落的?古人也有过在这般的天气里“约客不来过夜半,闲敲棋子落灯花”的嘘叹,我就疑心那被约的人一定是专注于听雨了:“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,”谁能不沉浸?而这时,江南的田野上,油菜花可是开得炽烈,黄黄的灿烂了田野,幽幽的染香了田野。男人、女人还有小孩就光着脚丫在酥软的田塍上走,你是城里人,也走。这时候轻悠悠走在你前面的是一个穿着花衣裳的女子。脚步匀得很细,阳光便被她踏得碎碎的。
江南是一个几千年不醒的梦,朱漆的木桨拍不出细碎的鼾声。江南是一个莲藕色的市井故事,讲完一个引子又接上一个引子。河姆渡女子的花纹陶釜很大,盛着网住的鱼和裹虎皮少年的钢叉,陶釜碎成一个悲壮的夜,鱼死了。独木舟搁浅在迷乱的月光下,这是开始的故事也是一个故事的开始。从此,就有一千个叫西施的浣纱女,讲着一百个吴越的故事,讲卧薪尝胆讲吴王金钩越王剑,讲伍员被挂在姑苏城头的嘲笑――他的雪髯皓发是一个过昭关的故事。
江南没有呓语般的驼铃和迷漫的黄沙,却一样有夕阳般的血和满布杀机的栏栅。江南的黄梅雨是一杯浓醇的情泪,啜尽了哀怨却啜不尽爱的淀积恨的溶化。每一个江南女子都是一首委婉的竹枝词,唱着水一般的柔弱火一般的热烈,款款地舞入柳三变和李易安的情思,隋炀帝的大龙舟在江南沉没,一群天真的吴越娇娃牵着一个王朝的纤索。
江南的柳絮总是发芽,江南的枫叶只能分隔一串永不结尾的神话,岳武穆的满江红只能在黄龙府吟唱,南渡的十二道金牌在天堂里凝成一行永恒的清泪,且留作茶馆酒肆慷慨的嗟呀!金戈铁马的辛稼轩也上了江南的层楼,红巾翠袖搵不干英雄泪,吟不成气吞万里如虎却叹茅檐低小,不能了君王天下事也做不成白发翁媪。
鲁镇的乌篷船里撑出了大脚的吴妈,祝英台是否能化作蝴蝶谁也不能回答,雷峰塔倒了白娘子不再演水漫金山,别忘了江南有李香君也有鉴湖女侠。《山海经》里没有江南,江南是一个茶色的故事一个东方民族的梦幻。只要几千年后我们仍能唱,唱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,唱那个浓郁的江南故事。永远,永远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