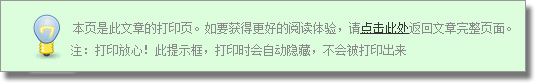一个30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,恢复高考以来,有319人陆续考上大学,4人考上清华。在享受荣誉光环的同时,村民们更承担着孩子学费高、就业难的压力。
“状元村”的教育账
边远、贫困的牛心屯村,36年间走出319名大学生,被人们称为“状元村”。小村的偏僻和“状元村”的显赫激起了媒体采访的冲动。
电话直接打给村支书白晓红却遭遇“一盆冷水”:不欢迎!理由是“没有用”。这反倒引起了媒体更大的兴趣。
300户人家200户贷款
村支书白晓红朴实、宽容,在一栋明显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米面加工厂旁边,很礼貌地迎接我们这些“不速之客”。绕过一个柴禾垛,走过一条长长的胡同,来到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高考状元白小玲的老家。2002年,白小玲就是从这条胡同出发,第一个走进了清华大学。
农家小院清洁规整,四间平房窗明几净。小玲的父亲白宝泉和母亲端来茶水。话题自然从小玲目前的境况谈起。
“小玲2006年一毕业,就到了上海一家国家级研究所工作。2009年和一个南开大学毕业生结了婚,不久前刚在上海买了房子。”白宝泉说着,显出很满足的样子。
然而,来白宝泉家串门的50岁的村民白景龙似乎没这么幸福。
他的大女儿2010年考上内蒙古民族大学,小儿子正在上高中,学习成绩始终在前几名。这本是件高兴的事,可是他为什么高兴不起来呢?
白景龙算了一笔账:大女儿上大学,包括学杂费、生活费,一年的花费至少两万元;小儿子一年也得一万多元。他家只有20亩玉米地,扣除成本,一年只剩2万元左右。为了孩子们的学费,农闲季节,他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,骑着摩托车,到40公里外的城里打工。赶上有活儿,一天180元;找不到活,颗粒无收。
白景龙说,孩子考上大学是好事,但学费太高,对农村家庭来说,确实是一个沉重的负担,现在,家里还欠银行4万多元贷款。
“牛心屯村300多户,在银行贷款的将近200户。”白宝泉说,现在是上学花钱,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,家里还得花钱。好多大学生毕业后都找不到工作,没有办法,只好到城里去打短工,甚至做力工。
尽管这样,也未能阻止牛心屯孩子坚定不移上大学的热情。村里有个女孩叫杨扬,三年前母亲患了乳腺癌,为了不影响她学习,父亲杨德军一直对她隐瞒实情。不巧,在高考前两个月,母亲病情加重,弥留之际,才把女儿叫到病床前。母亲在吃过半碗女儿递上来的鸡蛋糕后,与世长辞。坚强的女儿非但没有哭,相反,安慰爸爸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只是在回到学校,见到班主任老师石翠芬时,才放声大哭。石翠芬说:“她把我的心都哭碎了。”两个月后,杨扬倔强地走进考场,并顺利地考取了河南周口师范学院。
“状元村”的骄傲
在牛心屯村小学,珍藏着一本特殊的档案——《牛心屯村历届大学生登记表》,这张表是从该校第一任校长王宝山那里传下来的,记录着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以来,该校每年考上高等学府大学生的详细信息。这300多名学子,是这个乡村小学的骄傲。
9月6日上午,从白宝泉家出来,沿着坑坑洼洼的土路,走过一座漫水桥,慕名来到这所小学,不料,却再次吃到了“闭门羹”。校门被牢牢地锁上,斑驳的校牌已经分辨不出上面的字了,凭想象知道是校名,左边是蒙文,右边是汉字。隔着校门,看见校内有两排平房,操场左边是一排篮球架,右边是高高的旗杆。
校长白金莲“不失时机”地从平房里迎了出来,委婉地表示:学生正在上课,希望不要打扰老师和学生们。
轻轻地沿着走廊,观察了一下正在上课的四间教室。房间里昏暗潮湿,墙皮脱落,有大片大片水浸过的痕迹;教师的讲台和学生的桌椅不仅陈旧,而且破烂不堪,上面甚至有比拳头还大的窟窿。一排一排的“小脑袋”,仰着脖子在听老师讲课。
学校一间房的屋顶烟囱上冒出缕缕炊烟。知情人说:那是9名教师在热中午饭。这9名教师,大都是师范大学毕业,小学高级老师,在乡村工作多年,没有一个跳槽的。
在白宝泉家,村民们掰着手指头,一个一个数着牛心屯村小学历年来教师的名字:王宝山、白福山、田桂荣、白宝莲……一个一个数着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的名字:“文革”前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常宝龙,恢复高考后第一个走进清华大学的白小玲,第二个、第三个走进清华的白亮亮、白晶晶兄弟……眼神里充满了自豪和羡慕。
老教师敖兴东用每月30多元的工资供4个儿子“四子登科”;村民吴福德主业副业兼顾供养3个孩子上了大学;豆腐匠白庆华肩挑豆腐担子沿街叫卖,让两个孩子考进了清华……“现在牛心屯村出去的人,海陆空全有。有当船长、老师、医生的,有做局长、乡长、区长、副县长的,还有考上海事大学、航天大学的。”这句话是村民们最津津乐道的“流行语”。
“教育是一个长远的投资,不可能指望它立刻变现。”当过村支书的白宝泉说,农村家庭供大学生,投入越来越大,回馈越来越慢,甚至没有回馈。但是,把孩子培养成大学生,本身就是对国家的一份贡献。